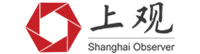将“书香上海”设为置顶星标
让书香与您常伴

什么是生存哲学?
汉娜·阿伦特 著
陈高华 译
文章原题为“What Is Existential Philosophy?”最初发表于Partisan Review, XVIII/1, 1946,后来重印于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New York:Schocken Books, 1994)。
生存哲学(existential philosophy)的历史至少可以往前追溯一百年。它于谢林的晚期作品和克尔凯郭尔,经由尼采而展现出无数新方向,不过其中许多方向至今尚未得到考察。它是柏格森思想和所谓的生命哲学的主要成分,在战后德国通过舍勒、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著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性阐明了现代哲学的核心关切所在。
简而言之,“生存”(existence)一词指的是人的存在(Sein),它与个体可能拥有的、通过心理探究可获得的性质和能力无关。因此,海德格尔曾经对“生命哲学”所做的准确评论——对于植物研究而言,“植物学”一词多余且毫无意义——也适用于生存哲学。不过,“生存”对“存在”的取代并非巧合,在这一术语的变化中触及了现代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黑格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全面性,为所有自然和历史现象提供了一个哲学阐释,并且把它们聚集在一个奇怪的统一体之中。他的哲学确实是“只在黄昏起飞的密涅瓦猫头鹰”,然而它为实在所提供的到底是居所还是监牢,无人曾有过明确判断。因为黑格尔一死,人们就立刻发现,他的体系代表着整个西方哲学的临终之言,至少就如下情形是这样:自巴门尼德以来,西方哲学——尽管它有各种转向和显而易见的内在矛盾——从未敢于质疑思想与存在的统一(to gar autoesti noein te kai einai)。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家,或者对他亦步亦趋,或者对他加以反抗,而他们反抗并感到绝望的正是哲学本身,即思想与存在之间设定的同一性。
这种追随性是一切所谓的现代哲学流派的共同特征。它们都试图重新确立思想与存在之间的统一,要么通过宣称物质的首要性(唯物论)或心灵的首要性(观念论)来达到一致,要么从各种角度出发创造一个带有斯宾诺莎印记的整体。
实用主义和现象学是晚近一百年来最新、最引人注目的哲学流派。在当代哲学中,现象学特别具有影响力,这一事实既不能简单地说是巧合,也不能单单归于这一流派的方法论。存在与思想之间的古老关系,向来保证着人们在这个世界的家园感,胡塞尔对这一关系的重建尝试采用了一条迂回路径,即假定意识的意向性结构。由于每一个意识行为天然地会有一个对象,因此我至少能肯定一件事,即我“拥有”我的意识对象。这样,存在问题,更不要说实在问题,就可以被“括起来”。作为有意识的存在者,我能够设想一切存在者,而作为意识,我就是世界的存在,当然是以我自己的人性样式(被看见的树,作为我的意识对象的树,并不必定是“实在的”树;但它无论如何都是我的意识的真实对象)。
世界的挫败性(discomfiting nature)这种现代感觉向来源于这样的感知,即个别事物被撕扯出它们的功能背景(functional context)。对此,现代文学以及现代的诸多绘画作品提供了无可置疑的证据。然而,人们对这种不安感无论做社会学还是心理学的解释,它的哲学基础总是如此:我也身处其中的世界的功能背景,总能够对为什么会有桌子或椅子作出解释并加以证成。但是,它永远没法使我理解为什么是这张桌子。而且,正是这张桌子的存在,而不是一般的桌子,唤起了哲学式的震惊。
现象学力图解决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在对意识的现象学描述中,它把这些被撕扯出功能背景的孤立事物定义为任一意识行为都可以抓住的对象;而且通过这一“意识流”,它似乎重又把它们整合进了人类生活之中。实际上,胡塞尔甚至宣称,通过这一经由意识的迂回道路以及对所有实际的意识材料的综合聚集(一种普遍数学),他能够重建现已支离破碎的世界。这种通过意识的世界重建等于是一次再创造,因为通过这一重构,这个世界失去了它的偶然性质,也就是说失去了它的实在特征,即它不再作为一个给定的世界,而是作为一个人所创造的世界向人显现出来。
现象学的基本原则包含一种最原初和最现代的尝试,即为人文主义提供一个新的理智基础。正是与生活感觉的紧密相连产生了现象学,这一点体现在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写给斯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那封著名的告别信中,在信中他说,他偏爱“小事物”而反对说大话,因为正是在那些小事物中隐藏着实在的神秘。如果说古典主义是用魔法从感到陌生的世界召回一个新家的尝试——通过对古典形象完全严格的模仿,即对人在这一世界的家园感的模仿——那么,胡塞尔和霍夫曼斯塔尔都是古典主义者。胡塞尔的“朝向事物本身”这一用语正如霍夫曼斯塔尔的“小事物”一样,都是富有魔力的口号。如果我们还能通过魔法取得某物的话——在这个其唯一好处恰恰是所有魔法失效的时代——那我们确实应该从最微不足道和看似最普通的事物开始,从朴实无华的“小事物”开始,从朴实无华的语词开始。
毫无疑问,正是这一显而易见的朴实性,使得胡塞尔的意识分析(雅斯贝尔斯认为这种分析与哲学无关,因为他不需要魔法和古典主义)对年轻的海德格尔和舍勒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即使胡塞尔在具体内容上对生存哲学了无贡献。胡塞尔把自己并不真正身处其中的现代哲学从历史主义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胡塞尔的影响只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性这一被广泛接受的信念是对的。黑格尔之后,在一种对历史的极端强烈兴趣的影响下,哲学似乎退化为对如下可能性的沉思:历史显现了某种内在法则。至于这种沉思怀着乐观还是悲观情绪,它认为进步不可避免还是认为衰落已然注定,在这里都无关紧要。关键仅仅在于如赫尔德(Herder)所说的那样,人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像是“只能在命运之轮上爬行”的“蚂蚁”。然而,由于胡塞尔对“事物本身”的关切中断了这种无聊的沉思,并坚持把现象上可证实的事件内容与其起源分隔开来,就形成了一种解放效应,因为人自身,而不是人陷于其中的历史、自然、生物或心理之流,再次成了哲学的主要关切所在。
哲学的这一解放反响很大,但是胡塞尔自己完全没有历史感,因而从未真正理解他的这一否定(negative)成就的诸多意蕴。实际上,这一成就比胡塞尔的肯定(positive)哲学重要得多。在这一哲学中,胡塞尔试图在所有现代哲学都未能让我们安心的主题上宽慰我们,即人被迫肯认一种自己没有创造而且与其本性相异的存在。通过把这一异质的存在转变成意识,他试图为这一世界再次赋予人的外观,就像霍夫曼斯塔尔一样,试图用小事物的魔法在我们之中再次唤醒对世界旧日的温柔。但是,让这种现代人文主义、这种朴实表述的善良意愿毁灭的,是同样现代的傲慢,这种傲慢不仅奠定了现代人文主义,而且希望——或者隐秘地希望,比如霍夫曼斯塔尔;或者直率、天真地希望,比如胡塞尔——最终以这种十分不显眼的方式成为人不可能是的样子:世界和人自身的创造者。
与胡塞尔傲慢的谦逊相比,原创性的现代哲学力图以各种不同方式接受如下事实:人不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此外,在最好的情形下,这种现代哲学试图把人置于谢林(谢林这样无疑是对自己思想的典型误解)为上帝保留的位置:“存在的主人”的角色。
就我所知,现代意义上的“生存”一词首次出现于谢林的晚期著作。谢林非常清楚,当自己提出“肯定哲学”作为一种对“否定哲学”、对纯思想的哲学的反制力量时,所反叛的是什么。他用以作为肯定哲学的出发点的是“生存……(它)最初具有的只是纯粹的那一个(the pure That)”。他清楚,经由这一步,哲学最终离开了“沉思生活”。他知道,正是“这个我(the I)给出了方向转变的信号”,因为纯粹思想的哲学,由于未能“解释事件的随意性和事物的实在性”,已经“使这个我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可以说,这种绝望是现代一切非理性主义、现代所有对心灵和理性的敌意的背后原因。
现代哲学始于如下认识:什么(What)永远无法解释那一个(the That);它始于对内在空洞的实在无法抑制的震撼感受。实在所显现的所有属性越是空洞,那么就越直接越赤裸地显现了关于实在唯一剩下的兴趣:那一个。这种哲学之所以从一开始就盛赞机遇(chance),认为实在正是通过这种形式直接把人看作是不确定的、不可理解的和不可预测的,原因就在于此。而且,这也是雅斯贝尔斯把那些驱使我们进行哲学活动的死亡、罪责、命运和机遇明确为哲学的“临界处境”(border situations)的原因,因为正是在所有这些体验中,我们发现自己无法通过思想逃避现实,或者解答其种种神秘。在这些处境中,人认识到自己不能依靠任何具体事物,甚至不能依靠自己的一般局限,而只能依靠如下事实:他存在(is)。
由于essentia(本质)似乎与existentia(生存)没什么关系,因此,现代哲学厌弃探究万物是什么(What)的科学。从克尔凯郭尔的观点来看,科学的客观真理无关紧要,因为它与生存问题毫无关系。至于主观真理,即“生存之物”的真理,则是一个悖论,因为它永远不可能客观、普遍有效。如果存在与思想不再是一回事,如果思想不再使我们穿透万物的真正实在,因为万物的性质与其实在毫无关系,那么科学就可以是任意样子;它不再向人揭示任何真理,也不再有任何让人感兴趣的真理。这种对科学的厌弃常常被误解为是一种源自基督教的态度,主要是因为克尔凯郭尔。但对这种热衷于实在之所是的哲学而言,为了一个更真实更好的世界,关键不在于贬低灵魂拯救而专注于世界万物[比如好奇(curiositas)]。这种哲学想要的显然是这个世界,然而这个世界唯一的重大缺陷是它丧失了实在性。
思想与存在的统一预设了本质与生存之间已然确立的一致;也就是说,一切可思考之物都存在着,而一切存在之物因其可知而必定是理性的。然而,康德这位现代哲学的奠基人,尽管是秘密的奠基人,而且直到如今仍是哲学王国里的秘密国王,他粉碎了这个统一性。康德揭示了内在于理性结构中的二律背反,由此夺去了人在存在那里拥有的那种古老的安全感;而且,通过对综合命题的分析,他证明在任何一个表述实在的命题中,我们都超出了给定之物的概念(本质)。甚至基督教也没有侵犯这种安全感,而只是把它重新解释为“得救的神圣计划”。可如今,人们既无法确定世俗的基督教世界的意义或存在,也无法确定古代宇宙永恒在场的存在,甚至aequatio intellectus et rei(知识与事物相符)这一传统的真理定义都无法维持。
在康德彻底变革西方的存在概念之前,笛卡尔已经用一种非常现代的方式提出了实在问题,只是他给出的回答完全还是传统的路子。存在本身是否存在,这完全是一个现代的问题,然而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这个回答却完全不得要领,因为正如尼采所指出的那样,这个答案根本证明不了思我(ego cogitans)的存在,它至多能够证明的是我思(cogitare)的存在。换言之,从“我思”中根本就无法产生真正活生生的我,而只能有一个作为思想之造物的我。这正是我们自康德以来所知的关键。
康德摧毁了思想与存在的古老统一,从中能够获得的衍生之物,要比我们在世俗历史中得到实现的多得多。康德对上帝存在的存在论证明的驳斥,摧毁了对上帝的理性信仰(它基于这样一个命题:理性可通达之物必定存在),这种信仰不仅比基督教更为古老,而且可能自文艺复兴以来更加根深蒂固地植根于欧洲人的头脑中。因此,所谓上帝在世界中消失,所谓我们无法理性地证明上帝的存在,不仅对基督教有严重后果,对古代哲学的观念亦然。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中,人处于任由解释的“遗弃”状态或“个人自主”状态。对于每一个现代哲学家——不只是尼采——而言,这个解释成了其哲学的试金石。
可以说,黑格尔是最后一位老派哲学家,因为他是成功避开这一问题的最后一位哲学家。谢林则标志着现代哲学的开端,因为他明确说自己关注的是“需要幸运之神”……“存在之主”的个人,这里所谓的“个人”,谢林指的是“摒弃了普遍的个人”,即真正的人,因为“欲求幸福的不是作为共相的人,而是那个个人”。这种关于个人追求幸福的直率表述令人惊讶(在康德蔑视对于幸福的古老欲求之后,如此重申对于幸福的忠诚绝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它所包括的远不只是想要回到上帝保护的急切愿望。康德在摧毁古典的存在概念时未能明白的是,他不仅让个人的实在而且让一切事物变得有问题。实际上,他暗示了谢林后来明确表述的东西:“根本不存在普遍,只有个别,普遍的存在(Wesen)只有就其作为绝对的个别(Einzelwesen)时才存在。”
根据这个直接源自康德的观点,人被切断了与绝对的、理性可通达的理念和普遍价值领域的关系,被抛入了一个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持的世界之中——他的理性不可依持,因为它显然不足以理解存在,他的理性所追求的典范不可依持,因为这些典范是否存在无法得到证明,普遍共相无法依持,因为它们只有以其自身的形式才能存在。
从此开始,“生存着”(existing)一词就被作为纯思想、纯沉思的对立面使用;它被看作是具体的,从而与完全抽象之物相对,就像个别与完全的普遍之物相对。由此而来的结果就是,自柏拉图以来只用概念思考的哲学,如今丧失了对于概念的信仰;可以说自那以后,哲学家们从未完全摆脱因耽于哲学而感受到的那种良心有愧。
康德摧毁古老的存在概念,其目的在于确立人的自主,他称之为人的尊严。他根据内在于人的法则理解人,并且把人从存在的普遍背景[人只是其中一物而已,哪怕人是思考之物(res cogitans),而非广延之物(res extensa)]中拽了出来,可以说,康德是做出这种努力的第一位哲学家。这是莱辛所谓的人的理智成熟的哲学表述,因此这一哲学宣言与法国革命一致绝非巧合。康德确实是法国革命的哲学家。正如它对于19世纪的历史发展至为关键一样,它对于后康德哲学的发展也至为关键,在19世纪,没有什么比关于“公民”(citoyen)的新的革命概念消失得更快,同样地,在后康德哲学中,没有什么比这个关于人的新概念消失得更快,几乎尚未开始成形就已消失不见。
康德对古老的存在概念的摧毁,这还只是做了一半的工作。此外,康德还毁灭了存在与思想的古老同一性,以及与之伴随的人与世界之间的预定和谐观念。他没有摧毁反而暗中保留的,是另一个同样古老且与和谐观念有着紧密关联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给定的存在,而人总是要服从这一存在的法则。只要人在存在中有一种安全感,在这个世界有一种归属感,并且至少能够理解存在和世界的进程,他就能够忍受这一观念。古代世界、实际上整个西方世界直到19世纪的命运观念都是基于这一感情(即直到新的感情的出现)。若没有人的这种骄傲,无论是悲剧还是西方哲学都绝无可能。甚至基督教也没有否认人能够洞见上帝的拯救计划;至于人自身把这一洞见归之于自己的神一样的理性能力还是上帝的启示,这并不重要。无论何种情形,人仍知晓宇宙的奥秘和世界的进程。
对于康德关于人之自由的新概念(它预示了现代主义者关于人缺乏自由的观点)而言,他对古典的存在概念的摧毁甚至更为真实。在康德看来,人基于自身的善良意志的自由,是有可能决定自己的行动的;然而,行动本身要服从自然的因果性法则,那是一个本质上与人相异的领域。人的行动一旦离开主观领域,即人的自由领域,进入客观领域,即因果性领域,它就丧失其自由因素。然而,就其自身而言自由的人却完全受到异于自身的自然世界运转的摆布,完全受制于对抗他甚至毁灭其自由的命运的摆布。这种不自由的自由,再次呈现了人位于世界中的二律背反结构。康德既让人成为人的主人和尺度,同时也使得人成了存在的奴隶。谢林以来的每一个现代哲学家都反对这种降格,但是现代哲学直到今天仍眷注于康德留下的这一充满悖谬的遗产:就算人成年后声称是自主的,他也完全被贬低。人似乎从未被提升得如此之高,同时又被降得如此之低。
因此,自康德以来,每一种哲学一方面都包含某种反抗因素,另一方面又或隐或显地包含某种命运观念。当马克思宣称自己不再去解释世界而要改变世界时,可以说他站在了一个新的存在和世界概念的入口,根据这一新概念,存在和世界不再是给定的,而是人的可能产物。然而就算是马克思,当他宣称自由乃是通过对必然性的洞见而获得时,也很快退回到了古老的安全之所,因而退回到了人,一个因丧失在世界中的位置而丧失其骄傲的人,此刻所谓的尊严对他几乎没有任何用处。尼采的amor fati(热爱命运)、海德格尔的决断(resoluteness),以及加缪的挑衅,即无视人在世界上的无根性这一人类境况的荒谬性而按自己的方式生活,都是通过退回到古老的安全之所进行自我拯救的尝试。自尼采以来,英雄的姿态已成了哲学的典型特征,这绝不是巧合,因为生活在康德所遗留给我们的世界之中,确实需要不小的英雄气概。现代的哲学家们凭着他们充满现代性的英雄姿态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能够做的只是把康德的思想推向其逻辑结论,而无法超出他哪怕一步。实际上,由于他们的逻辑一致性和他们所感受到的绝望,他们多半比康德还后退了好多步,因为他们全都(雅斯贝尔斯是个伟大的例外)在某一时刻放弃了人的自由和尊严这个康德的基本观念。
当谢林要求一个“存在的真正主人”时,他再次想在决定世界的进程上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而这样一个积极角色在康德之后已从自由人那里排除掉了。谢林又一次在一个哲学神那里寻求庇护,因为他接受了康德所谓的“人的堕落(Abfall)这个事实”,却没能共享那种让康德与这一事实和平共处的那份不寻常的平静。因为康德的这种平静(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在根本上源自他深深地扎根于传统,这种传统认为哲学本质上无异于沉思,当然,康德自己也在不知不觉地摧毁了这一传统。谢林的“肯定哲学”以神作为庇护所,因此神能够“抵消堕落这一事实”,也就是说,他能够帮助人恢复人在找到自己的自由那一刻丧失了的那种实在。
在论述生存哲学时,谢林之所以常常被忽略,原因在于没有哪个哲学家采用了谢林针对康德难题(主观的自由与客观的不自由)的方案。后来的哲学家(尼采是个例外)并没有诉诸“肯定哲学”,而是力图重新解释人类处境,以便通过某种方式再次让人回到那个剥夺了他的尊严的世界。不过,人的毁灭不只是命运使然,也是其自身存在的一个重要部分。人的堕落并非是完全由因果法则支配的、充满敌意的自然世界的过错,而是已然潜藏于人的自然天性。这也是为何这些哲学家放弃把康德的人的自由和尊严观念以及他的人性观念当作一切政治活动的调节原则的原因所在,而这反过来导致了如下情形:特有的忧郁成了自克尔凯郭尔以来最肤浅的哲学的特征。似乎把这种“堕落”理解为人的存在的内在法则比理解为受一个由因果性支配的外在世界摆弄,让人更可以接受。
编辑:段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