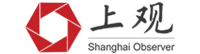复旦大学有一个学生社团——“大众印社”,我在印社做过几年篆刻辅导老师。那时候每年上下两个学期,每学期十堂课,每次上课我拎着一个大包,有印石、印谱等工具赶去校园。社团有近二十位同学,大部分为理科生,虽然每堂课两个小时下来他们握着刻刀在石头上刻出的线条与印文稚嫩得像他们纯真的笑脸,但我并不视他们为学生,而为朋友,所以上课时彼此插科打诨无比热闹,他们也没有顾忌,愿与我、与大家分享学校生活中的各种趣事。一晃我竟迎来送往好几届学生,其中不少毕业后至今与我保持着友谊,比如有颇具篆刻天赋的王近同学,2018年曾为我编辑的《陈伯吹书信集》做过不少资料查找工作;有担任过社长、却多次请假去舞龙舞狮的晓丹同学,那年寒假前最后一堂课,她作为印社代表给我写了一封感谢信;有每次认真上课、课后认真练习,偏在体育运动时视网膜脱落,不得不放下刻刀的轶聪同学。

近两年我去复旦的次数少了,偶尔会念及印社的同学们、念及那一个个午后步入校园的景象,这段缘分总在我心里闪着光亮,如同复旦,总在我生活的这一方土地、在宝山闪着光亮一般。
1905年开春,震旦学院爆发了震惊沪上的学潮,作为院长的马相伯与教会之间就课程设置和校务管理发生激烈的冲突,由此132名学生中130名签名退学,跟随马相伯离开了震旦学院。

马相伯
散了学,复校的念头一直盘算在马相伯心里,学生们的书仍是要读的,他为学生们的前途与命运担忧着。退学的学生们则组成了“沪学会”,请马相伯做会长,第一次集会他们在张园拍下了一张相片作纪念。不过没有经费、没有校舍,让马相伯陷入艰难的困境,于是他请来几位好朋友一起商量。这年5月,由严复领衔,袁希涛、萨镇冰、熊希龄、张謇、狄葆贤等28位校董具名,发表了《复旦公学集捐公启》,向社会各界募集办学资金。袁希涛是教育家、是宝山人,对宝山情形较为了解,期间他对马相伯建议吴淞有一处空了许多年的提镇行辕,不妨用来先做临时校舍。提镇行辕是江苏提督设在吴淞要塞附近的下属军务衙门,建于1877年,早已荒废。马相伯听后特意前往吴淞看了看,十分满意,他说:“地方很宏广,既远城市,可以避尘嚣;又近海边可以使学生多接近海天空阔之气。”于是打了电报给两江总督周玉山,请他将这旧衙门拨给复旦,再拨些经费。周玉山很快复了电:地方照拨,开办经费汇一万两银子。


复旦公学集捐公启(1905年,复旦大学档案馆提供)
马相伯将学校命名为“复旦公学”,起初意义为“恢复传承震旦公学”,后来听从学生于右任等人提议,取《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在自强不息、振兴中华。
经过一段时间对提镇行辕的修整,1905年9月14日,学校终于顺利在吴淞开学了。校舍虽然陈旧,规模倒不小。学校门前是一面照墙,照墙边上两根旗杆,东西两扇门,贴着门神秦叔宝和尉迟恭。进了仪门,是一个石板甬道,径直向前拾级而上经过一个平台,便到了大堂,那时用作礼堂,也就是饭堂。两庑有二三十间平屋,遥夹甬道,东西相向,做课堂、宿舍、办公室。大堂里面,前后有三进平屋,正中后进六七间,是校长室、教职员宿舍,其余都是课堂及学生宿舍。有一个化学实验室,又搭了几间板屋,做浴室、厕所、盥洗处,就在各宿舍的前廊。学校屋子总数在60间左右,8间讲堂、大小21间寝室、4间盥洗室、2间浴室、1间理发室、大小11间教职员司事仆役寝室、1间阅报室、大小3间理化室、1间会客室、1间厨房、2间储藏室、1间调养室、4处厕所等。只是学生宿舍不足,只够80人寄宿,学校不得不在淞沪铁路对面的吴淞怀远里另租几幢三间两厢房的石库门与几间沿着市河(今淞浜路)的房子做校外宿舍。学校门口没有火车站,不过火车司机似乎与学校有着默契,来来往往的火车经过复旦时总要探头看一看,如有人招呼,一定停下车,方便老师或同学上车下车。

吴淞时期复旦公学大礼堂侧面
(《复旦同学会会刊》1937年第6卷第78期校友节专)

复旦公学吴淞校舍复原图
(喻蘅作,复旦大学档案馆提供)
公学第一任校长为马相伯,聘请了严复、萨镇冰、袁希涛、狄平子等多位社会贤达担任校董,共同管理学校。第一年除震旦学院退学的老学生报到120人,另预备招收新生60人,令人意外的是,报名多达五百多人,马相伯、严复亲自主考,上午八点至十二点考汉文,学过西文的,下午二点至五点加考一次西文,最终只录取五十名,其中有一位来自宝山罗店镇的朱鹤翔,几年下来毕业赴了比利时罗文大学留学,归国后长期在外交部任职,并担任过驻比利时公使。
学校极为重视外语教学,除语文、历史、地理及伦理外,其他学科均采用国外课本,运用外语教学。复旦校章中详述阐述了外语教学的理念:一、外国历史、地理的名称,如翻成汉文,“叶音赘牙,不便记忆”;二、外国科学、哲学、法律等名词,“一时势难遍译,不如径用西文,较为简便”;三、“世界竞争日亟,求自存者,必先知彼为。先知彼者,必通其语言文字”;四、“西籍浩繁,非趁译所能尽收”“况泰西科学,时有新知,不识其文,末由取益,必至彼已累变,我尚懵然”。这些理念多半与严复有着重要的关联,1902年,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曾说过:“既治西学,自必用西文西语而后得其真”,他批驳那种认为学习外语就不爱国的论调,说:“此其见真与儿童无以异。爱国之情,根于种性,其深浅别有所系,语言文字非其因也。”

复旦公学章程
(1905年,复旦大学档案馆提供)
马相伯同时立下规矩,每逢星期日上午学生不准外出,由他选定多个演说题目学生们轮流练习,并把演说必需的方法,如分段、开始怎样抓住听众、结论怎样使人对于演说获得具体的了解,学生们都很感兴趣。
第二年马相伯辞职,严复继任,1907年,严复辞职,夏敬观继任,1909年夏敬观辞职,高风谦继任,1910年高凤谦辞职,复为马相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少复旦学生参加了革命军,加上经费停发,校舍又为光复军司令部占用,学校一度停办,到12月中旬,在无锡士绅的支持下,学校借惠山李公祠为课堂,昭忠祠为宿舍复学了,自此复旦离开了吴淞。1905年至1911年,复旦在吴淞七年,几任校长都聘请了具有真才实学、热心教育的学者担任教师,先后有李登辉、袁希涛、周贻春、赵国材等担任教学或主持教务工作,教学要求严格,共培养四届高等正科毕业生57人。有位学生回忆,他们印象深的老师有三位,一位是仪态整齐、举止健捷的李登辉,一位是头发梳得光亮、留着小胡子的平海澜,最后一位是于右任,容貌清瘦,整日穿着布大褂,讲国文讲的是司马迁的《刺客列传》,这让处在君主时代的同学们觉得多少有些稀奇。

宣统元年(1909年)复旦公学毕业生张彝卒业文凭
(复旦大学档案馆提供)
2019年,我策划了“文心灿烂·中国近现代学人手迹展”,大众印社一位学哲学的学生特地赶来宝山图书馆展厅,在参观中得知复旦大学最初诞生在这江海之滨时,顿时又惊讶又感动地在展厅转了好几圈,不舍离去。
作者:唐吉慧
编辑:潘乔雨
*转载请注明来自上海宝山官方微信
上观号作者:上海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