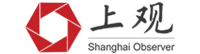距今4300多年前,晋南之地,表里山河,沃野千里。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下,在中原、河套、海岱、江汉、甘青、江浙等区域文化的互动碰撞与文化融合中,陶寺蕴化出一座煌煌都城。在这里,先民筑城建宫、敬授民时、阡陌交通、合和万国,初现王权礼制及早期国家的基本面貌。
8月20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陶寺遗址考古领队高江涛做客“南博讲坛”,以《陶寺与中华文明》为题,立足于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工作,带领观众走近陶寺,详细解读陶寺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贡献。

煌煌都邑:规模宏大,布局有序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县城东北约7公里处,汾河以东,地处太岳山脉余脉崇山北麓山前向汾河谷地过渡的缓坡状黄土塬上,整体处于三面环山一面向水的山川形势之中。
从文化分布、立都选址、多谷多畜、城址布局、观象授时、真龙呈现、圭尺定中、埋葬形态、范以铸铜、道路网络等十个方面入手,高江涛向观众讲解了陶寺考古40余年来的各种重大发现。

在至少280万平方米面积的遗址中,空前规模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墙、布局规整的墓地、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迄今为止最早的汉字、成组成套的礼器、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透过高江涛的讲述,一个早期国家都城的盛大气象跃然眼前:距今4300年左右,在晋南汾河之滨,水系密布之处,一座庞大的史前古城逐渐崛起。那是一座都城,城中恢弘的宫殿内,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这里城墙牢固,府库充盈,农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手工业进步显著,甚至出现了时代性的“尖端技术与核心技术”,数以万计的人口聚集于此处。城内布局有序,功能分区明显,宫殿区、贵族居住区、居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广泛的文化互动与交流成为当时社会的主题,其中暴力与战争更是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一系列发掘成果,使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逐渐显现出来。陶寺成为迄今发现的中国史前时期“都城要素最完备”的一座大型城址。
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与国家。从文明发展的角度考察陶寺遗址,高江涛表示,陶寺遗址与文明形成标准的“中国方案”高度契合。与此同时,陶寺遗址也为构建中华文明起源逻辑发展链条,奠定了基础。
陶寺模式:王权国家,礼制社会
文明呈现的模式与文明最终形成的内在原因密切相关。随着各区域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各区域文明形成过程中,社会形态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进而呈现出不同的“模式”。
不同于以红山、良渚为代表的神权国家模式,陶寺社会是王权国家,而非神权主导。“陶寺早期五座规格最高的大型墓的墓主明显是王者,此外,具有统一性规划的城址、较为完善的布局和功能的分区、重要的大型夯土建筑、宫殿类的建筑等,也都表明这里即是王者所居之都。”高江涛表示,种种迹象表明,以王权为核心的早期国家已经形成。

陶寺时期社会还是一个礼制社会。在陶寺遗址的大型墓葬中,鼍鼓、石磬、土鼓构成了一个固定的组合,在入葬时间相差100多年的墓葬之中,仍保持着组合不变、数量不变、位置不变的特点,形成固定的规制。而漆木器、厨刀、整猪或猪下颌骨的有意陈设摆放,似乎展现出的正是饮食之礼,同样显得仪式感十足。显然,规范现实社会中各阶层行为、身份、仪礼等社会关系或言“礼序人伦”的礼制在陶寺已经初步形成。
由此,以王权国家与礼制社会为特点的“陶寺模式”,与“红山模式”“良渚模式”“石峁模式”等,共同形成了所谓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模式。讲座中,高江涛强调,这种“多元一体”实质上,是一个多元演进并逐渐走向一体的过程,即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同时又是一体的。“从‘无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或许正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演进的最大特色。”高江涛说道。
文明特质:海纳百川,务实创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伴随着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逐渐产生、形成并成熟的智慧结晶。百年中国考古实践,尤其史前考古的事实证明,这些文明品质和精神内涵早在距今四五千年前,或已初步形成,甚至在更久远的年代已经萌芽。
讲座中,结合陶寺遗址出土的典型文物,高江涛与观众分析了陶寺文化的文明特质。
“海纳百川是中华文明传承至今的优秀品质,这在陶寺遗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高江涛表示,陶寺文明具有明显的兼收并蓄史前其他不同区域文明因素的特点。

用鳄鱼皮制作的鼍鼓、部分圆点纹彩陶以及随葬猪下颌骨习俗等,源于山东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粗体觚、玉兽面、玉笄等,与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及肖家屋脊文化同类器十分相似;玉琮、玉璧、v字形石刀,来自浙江良渚文化;晋陕高原石峁文化与陶寺文化之间,在陶器、玉器、铜器、建筑技术等方面均存在广泛互动……各自文化里,只有高等贵族才有资格享用的顶级“奢侈品”,被陶寺的“王”统统集中在自己这里。
“来自东西南北的东西汇聚于一处,说明陶寺的‘王’不仅对各地文明有着广泛了解,还大度地接纳了各地文明的成果,愿意把这些‘外来文化’的象征视为自己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一种胸怀天下的开放气度。”高江涛说道。
务实创新则是长足发展的文化基因。陶寺社会在宗教祭祀方面的投入较少,更多的是筑城造郭以“卫君守民”、观象授时以指导农事等,将主要力量放在生产性劳动领域,作风务实,客观上有利于其实力的积蓄和可持续发展。
高江涛将陶寺社会对周边其他区域先进文明的改造创新称为一种“扬弃式吸收”。如陶寺先民使用复合范铸铜器,成为辉煌的夏商周三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重要源头;而一些十分重要的玉器如玉璧、玉琮罕见像良渚玉器上繁缛的神人兽面及鸟纹,则成了素面佩戴功用的装饰品,并创新出多璜联璧、组合头饰、组合腕饰等新的象征物以凝聚族群。
“44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陶寺遗址是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典型遗址之一,陶寺文明呈现的特点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明的重要精神实质。”高江涛说道。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张洁茹/文 虞越/摄
上观号作者:交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