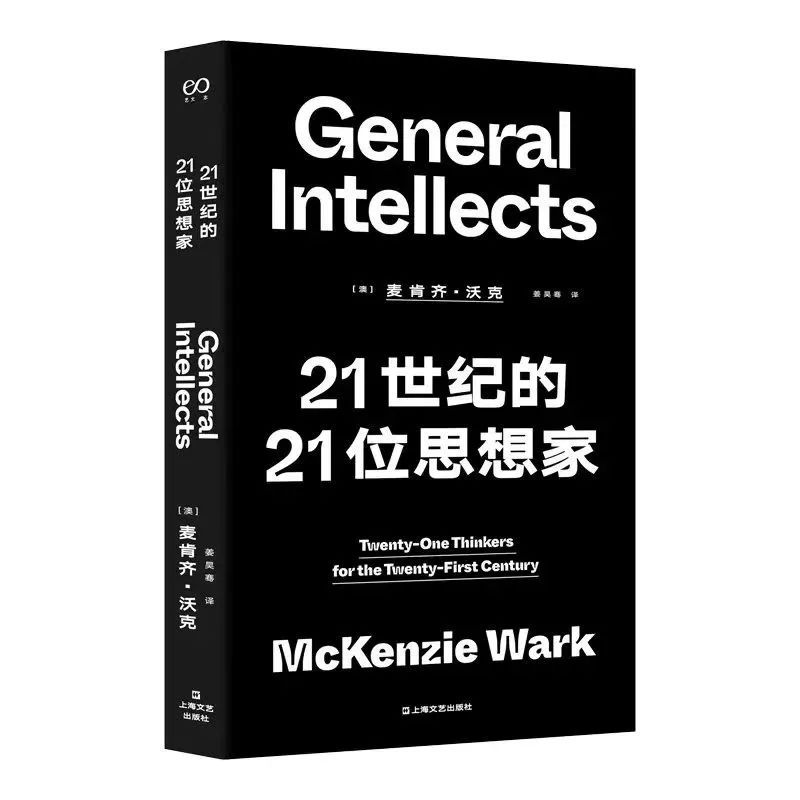
《21世纪的21位思想家》
[澳]麦肯齐·沃克 著
姜昊骞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1世纪的21位思想家》是一部介绍当代新思想的导论性书籍,作者用一本书的篇幅,评述了21位能够影响未来的思想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当今世界思想导图。
本书涵盖的话题包括文化、政治、工作、技术和人类世,评述的思想家有柄谷行人、齐泽克、朱迪·巴特勒、蒂姆·莫顿、”东浩纪、全喜卿等。麦肯齐·沃克别具一格的解读既表达了欣赏赞同,同时也提出思考,他期待一般知识分子共同编织一张协同的思想之网,以使人们理解,乃至改变这个世界。
《21世纪的21位思想家》入选5月文学报好书榜、世纪好书4月榜、《作家文摘》4月好书榜、界面文化一周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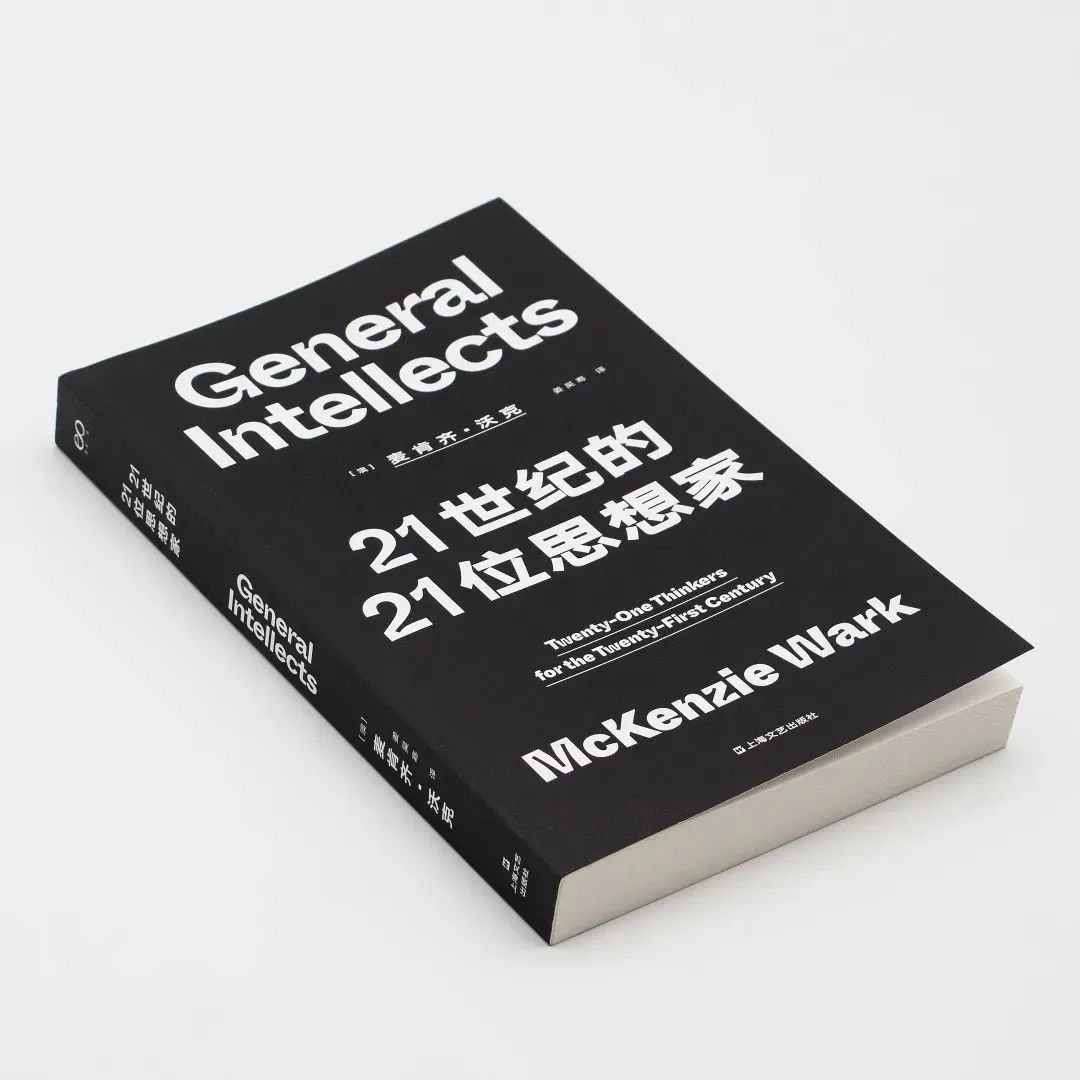
梅亚苏:绝对物的景观
文/麦肯齐·沃克
这是一块锆石,全世界最古老的石头。它的年纪大约有44亿年,而地球的年纪是45亿或者46亿年。因此,这一小块锆石,世界上最古老的石头,它经历得可多了。它来自得名自冥王哈得斯的冥古宙,因为从人类或者任何一种生命的角度来看,那都是一个相当不舒服的酷热时代——或者说,普遍的看法是这样的。
当地质化学家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与布鲁斯·沃森(bruce watson)研究这块小小的锆石时,他们发现了一些怪事。它是晶体,像其他所有晶体一样会生长,而在生长的过程中,也会纳入恰好在周围出现的其他原子 ——在它这里就是钛。温度越高,锆石的钛含量就越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测量锆石内钛元素的含量来了解锆石形成时的温度。
沃森和哈里森发现,这块锆石结晶时的温度在680摄氏度左右,这意味着它形成的环境里有水。沃森解释说:“任何岩石在有水的环境下加热——任何岩石,任何时间,任何条件——到650—700摄氏度时都会开始融化。这是唯一一种可预测性如此之强的地质过程。”
我自己不是地质化学家,只能相信沃森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我们有可能了解发生在人类出现几十亿年前的事情。那块小小的锆石正是甘丹·梅亚苏所说的原化石(arche-fossil)的一个好例子,是一个与我们这个物种毫无关系的世界的证据之一。
但是,这里还有一件让我感兴趣的事,尽管梅亚苏未必有兴趣。这个问题是:是什么让掌握原化石的知识成为可能?我可以思考原化石,我可以写关于原化石的文字。但是,思想和语言对它的存在都没那么重要。我们还要把另一个东西从它的存在中排除出去:一门叫作地质化学的科学,它存在于大学院系中,通过同行评议期刊和学术会议进行交流。某种意义上,它就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原化石的一种知识的思维和语言部分。
梅亚苏重视的是数学:这块锆石,一块原化石,它是对宇宙的一个可以数学化的描述。从大爆炸到星系、行星乃至小石块的形成,宇宙都可以用数学来描述。在他看来,这就意味着它们存在于思维或语言之外。宇宙可以存在于思考或写作的知识主体之外——只要你认为数学本身是实在的。
不过,我关注这块原化石的视角是:它是通过一种结合了劳动与科技的装置存在的,对宇宙过程的数学描述——乃至地质化学描述——都要通过这个装置来检验。上面提到的锆石经历了两次这样的检验。至少一次是科学测定年份,一次是测定内部结晶形成的钛元素含量。
我们可以将对世界的数学描述设想为非人的东西,不需要人类主体而存在。某种意义上,从原化石中产生出知识的技术工作也不需要主体,因为它是在装置上进行的,而装置是劳动与机器的结合体。我将这种对装置的依赖称为介人。我们之后会看到,它与数学描述的非人性并不是一码事。
一旦着手探究技术的部分,我们就会陷入硬核极客机械厂商网站的世界中。我在这里只提一家:cameca company。该公司的产品之一就是材料与地质科学电子探测分析仪:
sxfive 配备兼容钨和六硼化镧的通用型电子枪。持续射束电流调节,12小时内稳度 0.3%,确保长时段定量分析的可靠性。采用环形法拉第杯和静电偏转技术,精确测量射束强度。高压系统电压可达30kv,重元素可用。

我真是一句话都看不懂。我逛了不少同类厂家的网站,最后选择cameca的原因是:这家公司是做电影放映机起家的,在有声电影刚出现的时候,它就推出了能播放声音的放映机。后来,它转入科学仪器行业,不过在60年代曾短暂地回归人人交互媒体,推出了著名的点映机 scopitone。
吉加·维尔托夫让我们明白,电影用电影眼睛(kino-eye)取代了人的视觉。电影向人的视觉呈现的已经是某种介人的东西了。科学仪器甚至进一步拓宽了感知的范围,创造出了各种空间和时间尺度的介人性感知。比方说,仪器能感知和测定远祖化石,对人类的感官频宽和记忆力来说,这些化石是完全陌生的。机器感官充当非人中的介人领域,从而将人与人隔离开来。
如果我们忽略这种机器视觉,这种介人性的媒体,我们就剩下一个明摆着的选择。一方面,我们有人的思维和语言,或许还有人的感知。这是一个有限度、有边界的领域。另一方面,我们有非人的数学领域。暂且假设数学确实能够与绝对物相通,不受人类的限制。那么,我们就可以像梅亚苏希望的那样,将原化石视为存在绝对物的标志,这种绝对物甚至超出了非人的领域,只有数学才知道它。
然而,绝对物的数学性与人类的有限性之间还有别的东西,一种梅亚苏甚至没有提及的东西:装置。它既不是人,也不是非人,它存在于边缘的、不定的介人空间内。装置需要人类劳动,但不能化约为科学话语中的主体间领域。它还包括机器,机器感知和测量着远远超出人类世界的事物,记录着“广大户外空间”(the great outdoors)的存在,但并不与绝对物相通。
现在算是把装置问题拉了回来,那就可以问一问:当我们声称数学与绝对物相通时,这个绝对物是不是属于一个实在的世界。梅亚苏的思路是恢复对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区分。任何物的第二性质都是可感知的。我看到了、摸到了这个客体,但是,这果真就是关于它的要紧事吗?也许,这只是它在我们的感官中的表象?第一性质是客体的数学本质,独立于表象存在。或者说,这是继承洛克与笛卡尔思想的梅亚苏想要提出的观点。
在这个节点上,我们可以像杰伊·伯恩斯坦那样论证道,这种区分,这种对第二性质的隔离包含着现代性的关键。现代性以及它一整套理解和转化事物的装置产生,或许都有某种介人性的东西在里面,同时第二性质在装置中只发挥极小的作用。与阿多诺一样,伯恩斯坦认为第二性质的领域就是艺术领域。艺术从计算中拯救了感性。
或者这样:我们可以说,第一性质的概念暗藏玄机。按照梅亚苏的叙述,它们是物所固有的、数学形式的性质。因此,在哲学意义上,第一性质可以说是实在的。但是,除非它们还可以被测量,否则就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实在。测量第一性质需要装置,由机器和劳动构成的装置。借助装置,第一性质能像第二性质一样以可理解的方式——例如屏幕上的读数或者图表——得到呈现说明。其实或许可以这样说:要想让第一性质成为科学意义上的实在,那就需要借助第三性质使其成为可理解的第二性质。一件东西的第三性质就是装置对它的感知。这是一种介人性的感知,让非人的第一性质借助人的第二性质变得可理解。
梅亚苏之所以能够摆脱现象学的束缚,提出一种思辨哲学,原因在于对他而言没有一种两者之外的哲学。我暂且不会给这个第三种哲学命名。它关注的不是绝对,也不是意识,而是装置,它既不属人,也不是非人,而是人与非人之间的介人。
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
编辑:洪晖健
上观号作者:书香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