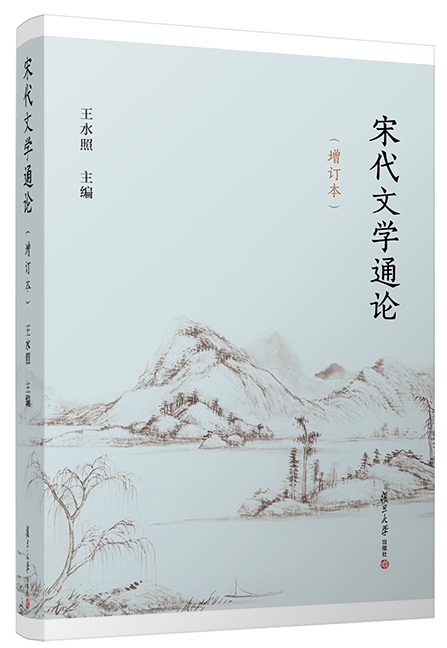
《宋代文学通论(增订本)》
王水照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南宋时期,外来军事打击所催生的国难意识,使当时体制内的入仕作家深感民族存亡的沉重与沉痛,表现在文学领域,抗金、抗元是最为集中的主题,慷慨昂扬、悲愤勃郁的基调贯穿于南宋诗坛词坛,这既为汉唐文学所未有,也为北宋文学所罕见。陆游的诗、辛弃疾的词双峰并峙,是南宋文学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也是爱国主义的精神瑰宝。
王水照先生是宋代文学领域的大家,今天我们选取先生著作《宋代文学通论》中的一节,来感受宋代士大夫词作中的情怀。
爱国与隐逸:士大夫情怀的写照
文 | 王水照
中国古代士大夫有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生存哲学。穷则隐逸,达则兼济,这也是宋词表现士大夫情怀的两面。一者,宋代士大夫即使贵为卿相,也常常表现出心存山林的高雅之志,如王安石等,他们就是在达时也可能有隐逸之作;一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宋代读书人对国家民族利益的关心远远胜于其他封建王朝的士大夫,太学生陈东的奋不顾身,南宋江湖文人群体的慷慨激昂,都是很好的证明,所以,“位卑未敢忘忧国”,穷者亦会有爱国之作。
爱国题材常常具体为边塞词和咏史词两大类词所描写。边塞词在宋代地位不高,宋人所编词选,如《草堂诗余》《花庵词选》《乐府雅词》《绝妙好词》等皆不选边塞词。但事实上,边塞词在唐五代就已产生,文人词如戴叔伦《调笑令》,民间词如《生查子》“三尺龙泉剑”等皆可视为比较成熟的作品。
北宋人的边塞词以范仲淹为最,其《渔家傲》一词写出了“燕然未勒”的悲愤与郁勃,为后代读者推许备至。
明人于《草堂诗余》之末附录此词,且评之曰:“范文正公为宋名臣,忠在朝廷,功著边徼。读此词,隐然有忧国忘家之意,信非区区诗人可伦也。”
但宋人的评价却不同,魏泰《东轩笔录》卷 11云: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事也!”
欧阳修批评范仲淹的一组边塞词——以首句皆为“塞下秋来”云云推之,根本只在“穷”,即所谓“边镇之劳苦”。而欧阳修赠王素的词则捷奏、贺酒、献寿,仿佛功勋就在眼前,唾手可得似的,难怪沈际飞以“不左迁不知县令之苦”讥之。
然而,欧阳修主张边塞词也要表现升平气象,以为边塞士兵的痛苦非“元帅之事”,又有其时代特点。
《东轩笔录》又云:“庆历中,西师未解。”欧阳修在晏殊席上作《晏太尉西园贺雪歌》有云:“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殊深为不满,对人说:“昔日韩愈亦能作诗词,每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如此作闹。”这里晏殊关于欧阳修诗的批评与上述欧阳修对范仲淹词的批评有着惊人的共通之处,边塞兵士之苦仿佛是诗词中所忌言的,可想见其时代审美风尚。
这种风尚导致了北宋真宗以来虽边事不断,而现存于《全宋词》中的能称为边塞词的不过12首(9位作者),只占《全宋词》中北宋词的千分之二三。并且,在这仅有的12首词中,如黄庭坚《水调歌头》云“戎虏和乐也,圣主永无忧”,蔡挺《喜迁莺》云“太平也,且欢娱”,皆与欧阳修《渔家傲》断章之主旨相近。晁端礼《望海潮》“高阳方面”在夸张地赞颂幽燕一带“粉堞万层,金城百雉,楼横一带长虹”之外,又津津乐道于军中佳人锦瑟、玉笋轻拢的享乐生活。
如此习惯性的粉饰太平的作风,让词人和词的接受者完全沉醉于自己编造的童话之中,缺乏起码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作风甚至影响到并不算边塞题材的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上。
北宋边塞词中堪与范仲淹的《渔家傲》媲美的是武职出身的词人贺铸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词中真实地记录了“笳鼓动、渔阳弄”的西夏入侵事件,叹息自己志业不售,只能“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飞鸿”。此词虽非在边塞上所作,但其言边塞之事,故视之为边塞之作也是可以的。
不过,一旦“寰海清美”、“千岁乐昌辰”(赵构《满庭芳》)的童话被金人的铁蹄踏碎,昔日以塞下为边塞,此时却只能以江河为“边塞”了。
此时,则边塞之作开始蔚为大观。首先,有爱国将领李纲自誓:“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苏武令》“塞上风高”)岳飞浩歌:“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重头、收拾旧河山,朝天阙。”(《满江红》“怒发冲冠”)
而文学之士的边塞词更是呼天抢地——朱敦儒曰:“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水龙吟》“放船千里凌波去”)向子则曰:“天可老、海能翻,消除此恨难。频闻遣使问平安。几时鸾辂还?”(《阮郎归》“江南江北雪漫漫”)做过李纲行营属官的张元幹则既有文士“天意从来高难问”的悲怆(《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又有武将“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石州慢》“雨急云飞”)的豪情。
此后,则有张孝祥、辛弃疾、陆游,以及所谓辛派词人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或高呼“休遣沙场虏骑,尚余匹马空还”的杀敌口号(张孝祥《木兰花慢》),或记载“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的战争经历(辛弃疾《鹧鸪天》),或传达“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的胜利捷报(张孝祥《水调歌头》),或为出使的大卿助威:“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陈亮《水调歌头》)有为秋阅的儒将擂鼓:“拂拭腰间、吹毛剑在,不斩楼兰心不平!”(刘过《沁园春》)有对英雄的赞颂:“人虽死,气填膺,尚如生。”(刘过《六州歌头》)还有痛斥懦夫:“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刘克庄《贺新郎》)直到南宋覆亡前后,刘辰翁还在“甚边尘起,渔阳惨,《霓裳》断,广寒宫”的回顾中谴责贾似道“何面江东”(《六州歌头》)。陈人杰还在对边事的追忆与叹息中“剔残灯抽剑看”(《沁园春》)。
爱国词的另一大类是咏史题材。中国人总是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之中,甚至“六经皆史”,所以往往用史实来推演新的生活,词人也不例外。但是,咏史作为词的题材之一种,并不完全表现爱国主题,它在走向以爱国为主的过程中先是以表现个人情怀而出现的。
北宋范仲淹《剔银灯》首句便云“昨日因为蜀志”,交待作词的缘起与咏唱对象,他从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的史实,推导出要像刘伶那样沉醉于酒中的结论。
柳永《双声子》“晚天萧索”从夫差旧国的兴衰中,认同了范蠡江湖一扁舟的自由生活的价值。苏轼《念奴娇》自题为“赤壁怀古”,从对赤壁之战中的英雄们随时间推移一去不复返的思考中,发出了“人生如梦”的叹息。
秦观《望海潮》“秦峰苍翠”在对吴越之地历史的回顾中,获得了“最好金龟换酒,相与醉沧洲”的选择。
只有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摆脱了这种“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主题。他从金陵旧事的追忆中,告诫人们吸取逸豫亡国的教训。
。
所以,全方位地描述宋词的隐逸之作亦是颇为可观的:欧阳修在东颍之西湖一口气唱出了十个“西湖好”(《采桑子》),乃是言隐于山水的快乐;苏轼在黄州东坡使僮子击牛角唱“为米折腰”(《哨遍》),乃是言归于田园的快乐;王安石在用《望江南》词牌所作的《归依三宝赞》中表现的是隐于佛的快乐;辛弃疾《最高楼》宣言“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又曰“闲饮酒、醉吟诗”,乃是隐于诗酒的快乐。正如刘熙载所言,张志和《渔歌子》与李白的《菩萨蛮》《忆秦娥》不同,乃是以“乐”为情感基调的,所以,宋人隐逸词也以心灵的闲适、恬静与快乐为特色。
| 内容选自《宋代文学通论(增订本)》。
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水照
编辑:马泽泓
上观号作者:书香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