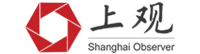✦ +
+
巴西
b r a z i l
2019年秋,我应邀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讲授为期三周的《中国电影史》课程。负责接待我的是该校人文学院的路易兹教授。一天下课后,他打算带我去里约市中心游览。在瓜纳巴拉湾的轮渡上,路易兹问我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说实话,那时我对里约这座城市几乎一无所知,事前也没做过旅游攻略一类的准备,就只能一切听由他来安排。
路易兹略想了一下说,那我们就去一些与电影有关的景点。第一站是一家名叫“虹膜”(iris cinema)的古董级影院,建成于1907年,是巴西现存最早的电影院,至今还在放映影片。这家影院保留了临街店铺式的传统格局,建筑外观带有浓郁的法国风格。

巴西现存最古老的电影院
虹膜影院
路易兹教授解释说,尽管里约曾是葡萄牙殖民地,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里的日常生活却充斥着法兰西文化的印记。影院有三层楼面,大厅地板是19世纪流行的色彩艳丽的贴花瓷砖。正中央是楼梯,左右边对称着向上延伸。两侧的护栏也是那种曲线繁复并散发着宫廷园林气息的铁艺装饰。大厅角落还隐藏着两架带栅栏门的老式电梯。路易兹说,这也是里约城内历史最悠久的两部电梯。

虹膜影院宫廷式铁艺楼梯
从虹膜影院出来,路易兹问我有没有看过巴西影片《中央车站》?我说当然看过,这部影片大概是我印象最深的巴西电影之一。《中央车站》问世于1998年,由著名导演沃尔特·塞勒斯(walter salles)执导,曾获第4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和第56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记得那时候我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用一台老旧的dvd播放器观看了这部影片。
说话间,路易兹带我来到这部影片的主要取景地——里约中央火车站。原本它是连接里约与首都圣保罗,以及其他巴西主要城市的交通枢纽,建成于1943年。如今,大规模的铁路运输已被繁忙的飞行航线与四通八达的公路客运所取代。中央车站也已转型为里约观光电车和城际轻轨的主要站点。眼前的景象,似乎很难再与那部著名的影片联系在一起了,唯有塔楼顶端那四面巨大的自鸣钟,还在向观光客们追忆着这座城市的前尘往事。
记得影片的海报上有这样一句话:“一个男孩在寻找他的家,一个女人在寻找她的心,一个国家在寻找它的根”。在剧情中,两个充满困惑和创伤的普通人在寻找孩子父亲的旅途中学会了爱与彼此信赖。导演试图通过孩子“寻父”的故事,来探讨巴西人文化认同与寻根的自我救赎之道。这一主题既蕴含着巴西人对于民族国家的一种自我指认和文化想象,也饱含着某种人道主义的普世情怀,即在一个充斥着丛林法则的乱世当中,人与人之间,如何用悲悯、宽容、善良和共情来达成彼此的和解与共融。对于经历过被殖民统治与军事独裁双重压迫的巴西人民而言,这似乎是放下沉重历史包袱,实现国家、民族浴火重生的唯一正途。

位于里约闹市中心的中央车站
按照路易兹教授的理解,被归属于“第三电影”(the third cinema)的巴西电影,其实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电影一样,在短短的百年历史中,同样主要聚集于去殖民化和对传统文化认同的重建上。表现在电影创作上,就是要努力避免对西方电影模式的一味遵从和模仿,尽可能透过影像叙事去呈现具有本土生活质感和巴西民间特色的文化属性。这种趋势,其实早在六十年代便已成为巴西电影始终贯彻与追蹑的目标。
譬如摘得第1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桂冠的影片《诺言》(1962),在剧情中,男主角相信是上帝让他的驴得以复活,为了表达谢意,他不惜背负十字架徒步远行,并最终以死殉道。该片导演是安塞尔莫·杜拉尔特(anselmo duarte),他想用这样一个荒诞与魔幻彼此交织的故事讽刺了教会的虚伪,同时也对百姓的愚昧、迷信、盲从以及某些高喊革命口号的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很明显的是,导演深受那个时代拉美左翼思潮的影响,对宗教信仰的阶级属性深信不疑。尤其在依靠宗教来寻求人生的救赎,还是面对压迫者攥紧反抗的拳头之间,导演毅然选择了后者。这不仅为他个人带来了某种世界性的认可与荣誉,也让这部影片成为开启巴西新电影运动的先声。
1963年,导演内尔森·帕雷拉·德·桑托斯(nelson pereira dos santos)拍摄了影片《艰辛岁月》。这部影片的问世,标志着巴西新电影运动的正式开启。这一时期,在时任左翼总统若昂·古拉特(joão belchior marques goulart)带领下,巴西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化运动,推行对土地、银行、财政等领域的改革,将石油化工等核心产业收归国有。上述政策的推出,对于巴西摆脱西方资本控制,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得到了巴西中下层百姓,尤其是劳工阶级的广泛支持。在这一社会运动和思潮的大力裹挟之下,巴西电影人也趁势开展了一场面对好莱坞与欧洲电影霸权的抵抗运动。而巴西新电影的问世,正是这场去殖民化社会运动最显著的文化事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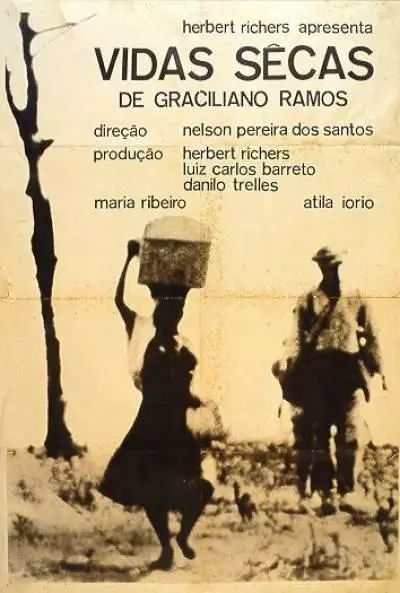
《艰辛岁月》(1963)海报
《艰辛岁月》的剧情,以一个家庭的遭遇折射出贫富差距巨大的巴西百姓的艰辛生活。导演受到20世纪40年代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影响,也选择把摄影机从摄影棚扛上街头,尽量使用自然光源。同时在人物对白上极为自律精简,把时间留给社会环境中的自然音效,以此来凸显人物与环境的冲突,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痛楚与挣扎。在导演看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所倡导的电影语言和语法,因为取法现实主义原则,天然具有无产阶级的属性,非常有利于揭示巴西无产者的生存现实。在一些学者眼中,这也让这部影片被打上了深刻的人道主义的烙印。
巴西新电影的问世,迅速将巴西电影推上了世界舞台。譬如导演格劳贝尔·罗恰(glauber rocha)分别以《黑色上帝,白色魔鬼》(1964)、《痛苦的大地》(1967)和《安托尼奥之死》(1969)三部影片,先后三次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

杰出的巴西电影导演
格劳贝尔·罗恰(1939-1981)
不同于桑托斯的深沉与朴素,罗恰更像是一个激情澎湃的青年革命者,他以电影为武器,对巴西过往的殖民血泪史进行了大胆地控诉,对独裁的军政府的种种罪行也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抨击与揭露。他偏爱在自己的影片中营造一种虔诚甚至狂热的宗教氛围,擅长在色彩、音乐等视听元素中融入巴西本土的民俗元素,以恣肆奔放的巴西符号来着力编织出一种属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寓言。
有人直接把巴西新电影称为是一种巴西电影的“本土化运动”。从去殖民化的角度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参与这一运动的导演,往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注重挖掘巴西本土文化元素,不论是宗教传说、民间故事还是下层百姓的现实生活,都是他们最为钟情的选题和表现素材。正如导演桑托斯所言:“巴西的民族文化不同于那些肤浅陈腐,带有殖民色彩的精英文化,我们要在电影中反映本民族的文化,捍卫人民大众的政治理念和民主精神。”从今天的眼光看,这句话甚至可以视为上世纪六十年代以降,巴西新电影运动所确立的一种光荣而神圣的传统。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沉寂了20多年的巴西电影,再一次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先后涌现出布鲁诺·巴列托(bruno barreto)、沃尔特·塞勒斯、费尔南多·梅里尔斯(fernando meirelles)和卡迪亚·兰德(katia lund)等一批优秀的本土导演。与老一代导演相比,他们的电影观念和艺术风格都更加前卫、独特,同时又具有开放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经验。
2002年,由沃尔特·塞勒斯担任制片,费尔南多·梅里尔斯和卡迪亚·兰德共同导演的《上帝之城》横空出世。影片以社会动荡六、七十年代为背景,讲述了里约贫民窟中帮派少年挣扎成长的残酷故事。导演们用摄影机记录了那段黑暗血腥的历史,以性和暴力,以及充斥着少年荷尔蒙气息的视听风格,深刻地诠释了巴西这片既古老又年轻的土地所蕴藏的变革的力量。该片获得了包括奥斯卡最佳导演奖、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英国电影学院奖等多项顶级国际奖项的提名,跻身为世界电影史上不可忽略的经典影片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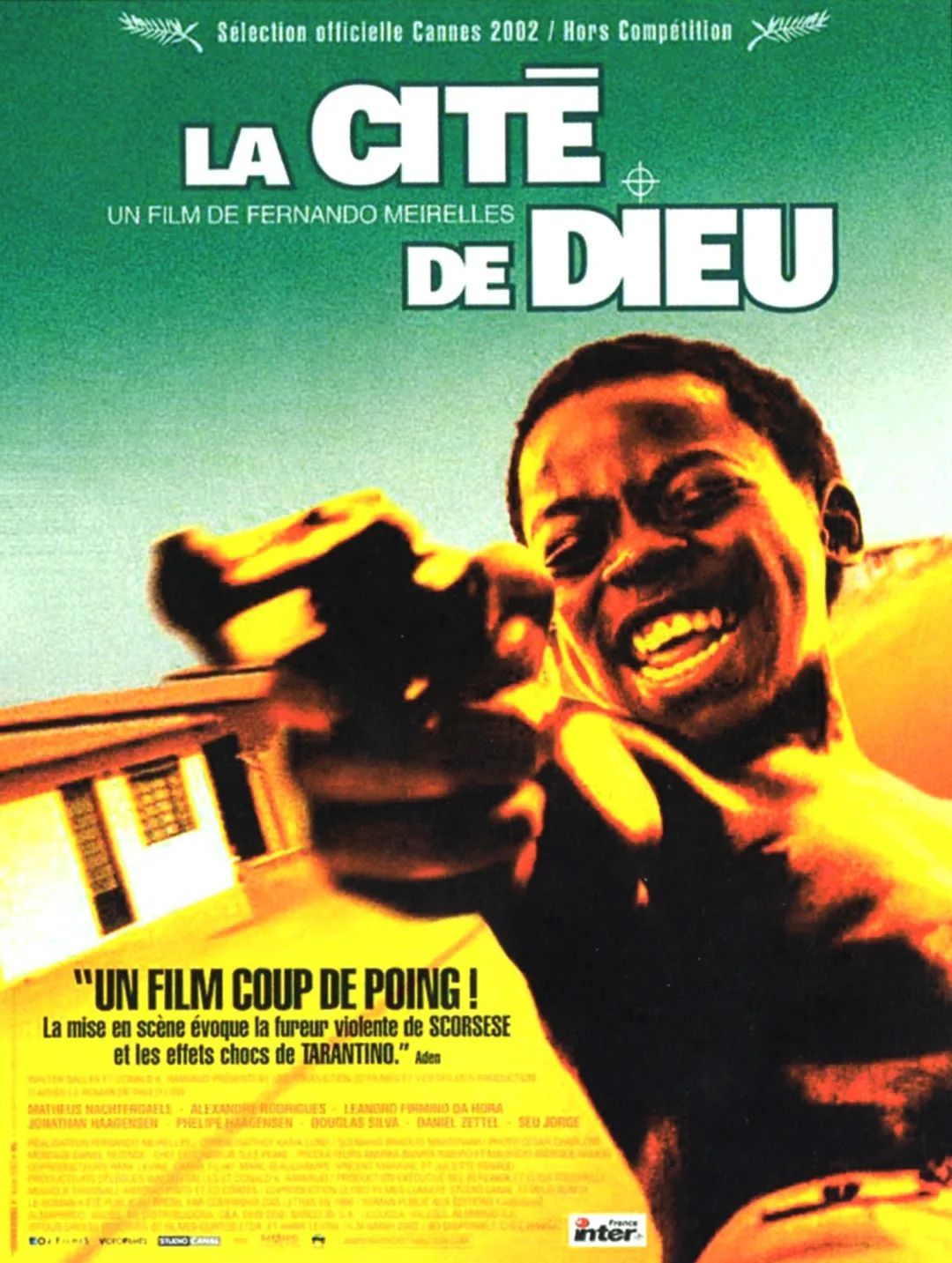
《上帝之城》海报
近年来,随着金砖国家电影节的举办,巴西电影的最新成就又一次被新一代全球影迷所熟悉。2017年,在第二届金砖国家电影节上,由罗伯特·柏林厄(roberto berliner)执导的影片《尼斯:疯狂的心》(2015)荣获了最佳影片奖(该片还曾获得第28届东京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麒麟奖);由安娜·穆拉尔特(anna muylaert)执导的《第二个妈妈》则荣获评委会特别奖。《尼斯:疯狂的心》讲述了一位女医生大胆跳脱传统医疗手段,用艺术来治愈病人精神疾患的故事。剧情中的女医生尼斯,代表了那些获得了女性主体性的职业妇女,勇敢地与男权主流社会相抗争的时代进步趋势。而《第二个妈妈》也以女性的视角,讲述了一对母女以亲情和善良消除误解,彼此宽容的温暖故事。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由半个世纪前的巴西新电影所确立的现实主义精神,依然在今天新一代巴西导演的作品中得到了延续和坚持。与前辈一样,他们秉持着电影工作者的道德良心,用一种顽强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切的人文关怀来关注现实。正是这群略带天真和稚气的巴西影人,经过半个世纪的筚路蓝缕,才让巴西电影成为第三世界文化的优秀代表之一。今天,当我们用深情的眼光回望这个国家的历史,以凝重的笔触书写巴西电影的坎坷历程的时候,那些用一卷卷电影胶片铺就的,难道不正是这个国家沧桑曲折的历史过往和充满希望的未来图景吗?
作者:石川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观号作者:上海国际电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