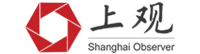《本雅明传》
[美]霍华德·艾兰、迈克尔·詹宁斯 著
王璞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两位资深的本雅明研究者兼本雅明文集编者、英译者艾兰和詹宁斯以九百页之巨的篇幅,巨细靡遗地描绘了本雅明的一生,以及20世纪初那个从昨日世界走向两次大战间的恢弘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版图。对有关传主的所有现存资料——论著、信件、日记、他人的回忆——一网打尽式的研读为这本传记的成功奠定了基础。精准细致地讲述本雅明的生命历程之外,本书对传主思想的阐释也非常到位,评论者誉之为“指引我们探索本雅明思想迷宫的可靠地图”。
近日,上海文艺出版社《本雅明传》入选中华读书报8月好书榜。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本雅明传》节选
文/霍华德·艾兰、迈克尔·詹宁斯
本雅明在尼斯已经写信给马克斯·霍克海默,再次申明他对研究所的全身心投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把自己的工作和研究所的工作尽可能密切和富有成效地联系在一起更紧要的了。”不论他内心深处有过怎样的保留意见,本雅明很清楚,研究所已经成为他的主要依靠。不仅研究所的《社会研究杂志》已经成为他发表自己作品的最重要阵地,而且研究所从1934年春开始提供的津贴是他30年代唯一的定期收入。
1935年4月,一系列情况把本雅明和研究所绑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并为他的拱廊街研究提供了关键动力。他到达巴黎不久后,终于有了一次会面,从冬天到早春他在这一会面上寄托了太多的希望。这就是和研究所的一位主任弗里德里希·波洛克的会面,它带来两个重要结果。
其一,它至少在短期内缓解了本雅明最严重的经济忧虑。波洛克让本雅明的月津贴(从1935年4月到7月)在四个月中翻倍,从500法郎涨到1000法郎,此外,还支付了500法郎现金,作为他在巴黎的安家费。
而且波洛克还对拱廊街研究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建议:本雅明应写一篇此计划的提纲。到此时为止,本雅明只是以最为概括的方式对霍克海默及他的同事谈论过他计划中的著作:对那些材料 ——“关于它们,我零星地提示过,但从没有透露多少”——的一次系统性评估现在对他和他的支持者来说都是必要的了。
本雅明立即抓住这根递到他手里的智识生活的救生索,一头扎进写作提纲的工作之中。悖谬的是,此文的写作受益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年度闭馆:本雅明没有机会再沿着那些材料的线索追踪新的路径,只得坐在他的房间里写作,手边只有他的拱廊街计划的海量笔记。这次的工作在接下来一个月中得以相对快速地完成,成果便是《巴黎,19世纪的首都》,它也是关于拱廊街综合体的两篇浓缩性展示中的一篇(第二篇于1939年用法语写成)。
提纲的完成恢复了本雅明的自信乃至他活下去的意愿 —不论是多么暂时:“在这一作品中,我看到了不要丧失为生存而斗争的勇气的首要原因,甚至是唯一的原因。”本雅明给维尔纳·克拉夫特的信中谈到,他能够以惊人的速度给他汇集的各种不同的笔记和想法赋予秩序 —一次“结晶”:“这个计划如土星运行般缓慢,其最深层的原因在于大量的想法和意象都必须经历全面的大变动。它们来自非常遥远的时期,那时我还进行直接的形而上学,其实是神学方面的思考,而大变动是必要的,这样它们才能充分地滋养我现在的倾向。这一过程无声无息地发生着;连我自己都极少察觉,以至于当 —作为一次外部刺激的结果 —我最近在仅仅几天中就把研究计划写了下来,我也感到极为惊讶。”他向阿多诺更为详尽地解释了这一计划的源起:
最开始是阿拉贡 —他的《巴黎农民》,每次夜里躺在床上阅读,绝不超过两三页,我的心就开始跳动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不得不把书放下……而为“拱廊街”而作的最初草稿也可以追溯到那时。—然后是柏林岁月,那期间,我和黑塞尔的友谊最珍贵的部分就是从关于拱廊街计划的无数交谈中生长起来的。正是那时,副标题“辩证童话”第一次浮现,而今天已不适用。这一副标题提示了在我当时的构想中这一作品的狂想曲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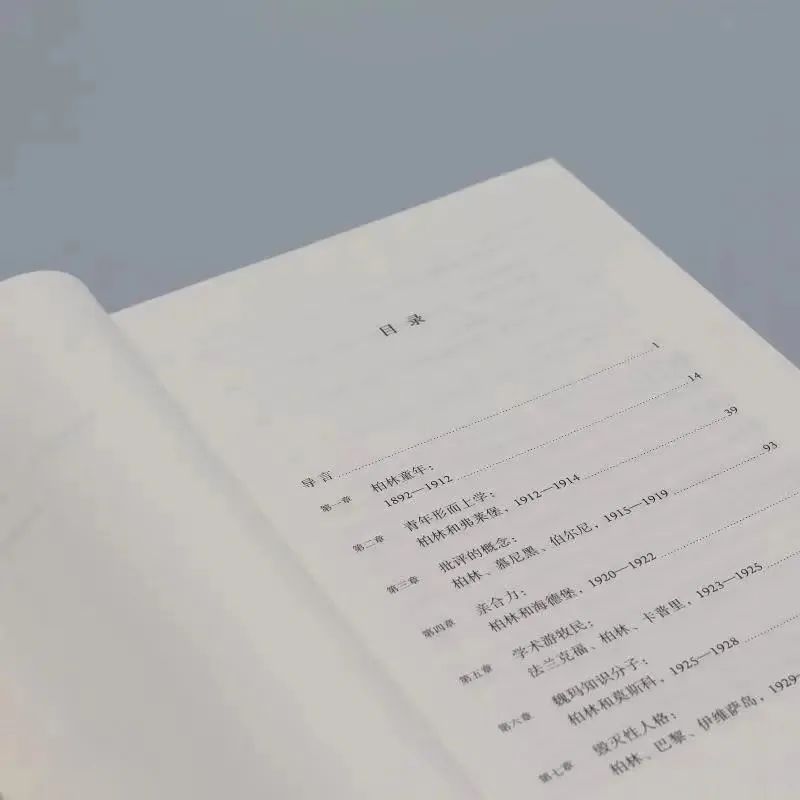
本雅明把拱廊街计划的早期工作定性为“狂想曲”式的,等于承认计划缘起于“一种幼稚地困于自然的哲学思考的古老形式”。而现在,正如他对阿多诺所说,这一计划则确然受惠于和布莱希特的相遇,而且他认定,这次相遇 —也即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与原创性的超现实主义视角的对峙 —所造成的“难点”都已经得到解决。
1935年提纲以一种高度浓缩、近乎速记式的风格写成,广泛地涉及一系列话题(从钢铁建筑和摄影技术到商品拜物教和辩证法停顿等理论),确立了历史人物形象(从夏尔·傅立叶和路易·菲利普到波德莱尔和奥斯曼男爵)以及19世纪的典型人物。
《拱廊街计划》的基础是一系列复杂的理论立场,本雅明在过去七年中将它们逐渐提炼出来,它们也表现为提纲中的统摄性范畴。而且,作为贯穿提纲的隐喻,拱廊街本身,那些微缩的大都会世界,也呈现出新意义:在一种结构性的含混状态中——既是室内空间,又是公共通道;既是商品展示的场所,又是城市休闲空间——它们提供了本雅明现在所说的“辩证意象”的最早范例。
在1935年,辩证意象被构思为“愿望意象”或“梦境意象”,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动态显影,在其中“新”被“旧”渗透,集体“既寻求克服但又试图美化社会产品的不成熟和社会生产组织的不充分”。在这一意义上,1935年提纲是从20年代后期开始就规定着这一计划的“社会心理学阶段”的最终产物。在提纲中,这些梦境意象证实了集体有能力预见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在梦境中,每个世纪都怀抱着关于下个世纪的意象,后者似乎与原历史的元素—即无阶级社会的元素——联姻了。储存于集体无意识中的无阶级社会的经验,通过与新的意识相渗透,产生出在生活的千种样态——从坚固耐久的建筑到昙花一现的时尚 —中留下痕迹的乌托邦。”
在他1929年关于超现实主义的论文中,本雅明已经假定,在过时之物中潜藏着“革命的能量”。1914年的演讲《学生的生命》开头一段确实也说出了相同的意思。在这里清楚阐明的也许更复杂的模型里,我们可以从乌托邦的痕迹——产生自新与旧的交错或撞击——中读出当代社会未被讲述的侧面。
《巴黎,19世纪的首都》是作为对社会现象的这种占卜式阅读的某种路线图而创作的。巴黎的火车站、傅立叶的法郎吉、达盖尔的全景画,以及街垒本身——所有这些都作为愿望意象在提纲中出现,这些愿望意象在自身之中保有一种具有革命潜力的知识。即便是那些被商品展示和交换所支配的结构与空间 —世界博览会、资产阶级的室内布置、百货商店和拱廊街 —也被表现为包含着社会变革的一种矛盾的可能性。
提纲还预告了更多:拱廊街计划本来还会包括一种深入的文类和媒介理论。报纸的民主潜能、政治上中立化的全景文学,以及摄影通过大规模复制对商品交换领域的拓展,这些都被处理为新的社会现代性的组成方面,它们和一种新的多视角观看方式一道,已经于19世纪中期之前在巴黎兴起。在提纲的总结部分,本雅明暗示了关于现代体验的综合理论,他的晚期作品主要专注于此。
在他对波德莱尔这一人物的思考中,本雅明预示了后来成为经典的那种对现代文学的解读——他把波德莱尔的诗歌呈现为对“异化者”具有转化力的“凝视”的反映。他把波德莱尔描绘为一个典型的世纪中叶的漫游者,当他没有顺着都市人流漂浮时,就在市场的门槛处徘徊不去——门槛理论是《拱廊街计划》的基础。
人群是“面纱”,透过它,熟悉的城市如幻景般向漫游者招手;漫步者时不时地遇到来自过往时代和遥远地方的鬼魂,他们躁动不安地布满日常生活的现象之中。波德莱尔的忧郁凝视因此代表了漫游者的感知的寓意模式,在漫游者的感知中,一座祖先的象征之林不断闯入流转的城市风景,而历史的客体,和任何时尚的客体一样,同时征引过去和未来,就如同重写本和拼图。
提纲罗列了——并没有分析——那些对后来他的波德莱尔解读很重要的母题:诗人对突然出现在人群中的穿丧服女子的震撼印象;他对印在巴黎的现代面影上的,新的而永恒相同之物的体验;他对地下巴黎的勾画,带着关于神话过往的地府回响。最后的部分,论及奥斯曼大胆而无情的城市规划或“战略美化”,展示了本雅明理解阶级冲突的最直白的尝试之一。
提纲收束于对辩证思维作为“历史觉醒的器官”的强调性确认,因为“梦的元素”在醒来过程中的实现——实现既意指“认出”,又意指“利用”——是本真的历史思维的范式。
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
编辑:沈阳
上观号作者:书香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