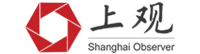《江南儒学的构成与创化》为“江南文化研究”丛书之一种,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何俊主编。本书以时间为序,分述江南儒学的孕生、唐宋变革与江南儒学的崛起、明清江南儒学的演化,以及江南儒学的现代探索。本书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学界给予江南儒学长久而深切的研究兴趣,使江南儒学的研究成为江南研究、儒学研究、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研究,乃至面向未来的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本次推送为本书第一章《为什么要研究江南儒学?》之节选,由何俊教授撰写。
好书•推荐

《江南儒学的构成与创化》
何俊 主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本书是“江南文化研究”丛书之一。在首章,着重说明江南儒学的提出、指义与时段,希望对江南儒学建立起一个整体性的框架,并试图呈现出一点江南性的思考。二至六章,分述江南儒学的孕生、唐宋变革与江南儒学的崛起、明清江南儒学的演化,以及江南儒学的现代探索,其间就明末江南儒学与西学专辟一章。本书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学界对于江南儒学给予长久而深切的研究兴趣,使江南儒学的研究成为江南研究、儒学研究、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研究,乃至面向未来的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为什么要研究江南儒学?
(节选)
文丨何俊
江南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现状构成了提出江南儒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直接的外部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中,江南的经济社会文化不仅位居整个中国的前列,而且呈现出强劲而富耐久的动力;源自江南的许多理念与实践不断被上升到国家层面,长江三角洲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彰显了江南作为国家根基的性质。江南所放射出的吸引力与引导性,表证着她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将富具影响,这一现实给上世纪中叶以来持久展开着的江南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以使江南获得更进一步的自我认知。江南儒学的概念由此催生,以期江南研究获得纵深推进。
当然,强调江南儒学研究的当代与未来性,并不等于这一研究的提出完全基于此。相反,江南儒学研究的当代与未来性是基于历史本身而产生的,尽管历史上没有以此命名的思想流派,甚或没有江南儒学这样明确的自觉。唯此,我们需要给予进一步的说明。
这个说明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国历史中的南北经济社会文化重心的转移及其延伸出的江南问题。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的南移是一个非常显著而早已引起历史中人,当然更引起现代学术研究的关注,相关的史料与研究汗牛充栋,毋需引征。这里,仅依钱穆在《国史大纲》中的梳理作一个简明的转述,以引起我们后续的讨论。《国史大纲》虽成于上世纪前半叶,但钱穆以其纲目体,将这个长时段的重大的历史显象勾勒得极为清晰。钱穆指出,中国历史上半段的重心在北方,下半段在南方,这个转移以安史之乱为节点,转移的过程则很长,似乎直到明代才完成。[1]钱穆从经济的指标,比如漕运、丝织业与陶业,到文化的各部分,比如应科举的人数、宰相籍贯人口,再到社会,如户口盈缩、行政区划的大小繁简,作了系统的梳理。[2]从这个梳理与论证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的南移不仅是毋庸置疑的史实,而且这个南移的过程最终结穴于环太湖流域的江南也是极其明确的。

▲钱穆
也许因为这个转移过程,尤其是环太湖流域的江南成为这个转移的完成标志直至明中叶才确立,所以才会在晚明出现陈子龙(1608-1647)那样的全面论证江南地位的系列文章。按照森正夫的研究,陈子龙论证的江南包括今日的江苏省南部、上海市、浙江省北部,即以长江下游南岸地区的三角洲为范畴的区域,其实就是环太湖流域。在多达七篇专文中,陈子龙不仅从综合地理条件、具体的水利与地质特征、土木建筑技术、养蚕丝织业、女性能力、水产资源、文章与艺术个性等各方面系统地论证了江南在历史过程中所确立起来的重要性,而且更从明朝政权本身的建立过程及其完整的政治设置,赋予了江南是伟大的明朝国家之根基的地位。换言之,陈子龙的江南论决不是就江南而论江南,而完全已是从整个中国的视野来强调江南的地位。[3]
不过,也正因为陈子龙的系列文章,可以反证江南作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的真正确立,虽然在事实上早已在形成过程中,但名份却要晚来很多,否则陈子龙也无必要作这样的系列文章,尤其他要以自设问答的文体来作辩明。这一名位晚于实情的现象似乎在提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江南已明确成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中心的事实面前,还需要去辩明它对于国家的根基地位呢?可能的解释也许很多,但从陈子龙自己设定的提问,结合我们的研究对象,似乎可以聚焦在两个解释上。其一是江南成为经济社会文化的重心只是一个偶然的暂时的结果,对于历史中的人而言,仍然存有重心回归的期待,因此并不认定江南已为重心,直到晚明已为定局,还需要陈子龙来论证。其二是江南固然已成为经济社会文化的重心,但其经济行为、社会组织、文化形态背后的思想系统不具有正当性,陈子龙在辩论中强调,作为国家根基的江南的确立,“实惟有吴风教固殊焉”,这个“风教固殊”在陈子龙的论证中当然是正面的,但在北方看来也许完全是负面的。[4]

▲《松江邦彦画传》中陈子龙画像
这便意谓着,作为一个区域,江南能否成为国家的根基?或者,江南为什么能够成为国家的根基?或者,江南是如何成为国家的根基的?自然便成为一个问题或者一个问题丛。由这样的问题丛出发,江南研究当然首先是一个区域研究的问题,但是由陈子龙的论证引发出已超越区域研究的性质,而是关涉到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及其内在动力的问题。这是江南研究得以成立的根本学理所在。
另一个方面则是聚焦到“有吴风教固殊”的问题。前述的江南问题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而“风教”则指向文化,尤其是狭义的文化核心,也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江南儒学。中国传统的文化主流虽然存有认识上的分歧,但我们却取儒家为主流的认识。从陈子龙的论证看,他虽然从自然环境一直论证到制度设计与安排,但最终却归之于“风教”,这其实就是我们提出江南儒学这个概念的历史依据。如果细细品味陈子龙的“有吴风教固殊”,可以体会到他一是从江南的整体性,即“有吴”来讲的,二是归结于“风教”的“固殊”,这个“固殊”正是江南儒学作为新的研究视域所需要去面对的,固殊的面相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固殊性?这样的固殊性为什么会导致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的南移?以及它是否在当代仍然存活,并能否引向未来?
总之,江南儒学确实是一个首先由外部因素所型塑而成的概念,但又是基于具有坚实历史基础的学理上的。
江南儒学的提出虽然具有现实与学理的依据,但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其内涵仍然是需要进一步界定的。这个界定首先涉及到如何理解作为空间的江南,其次是作为对象的儒学。两个问题都所涉甚大,这里仅先处理儒学的界定。
儒学是一个边界很不清楚的语辞。从广义上讲,即取其文化之义,则几乎涵盖传统生活的一切,尤其当研究一个区域内的儒学传统时,往往容易指向这样的广义。前述陈子龙所谓“风教”,便可以与此对应,虽然“风教”可以作比文化稍狭一些的限定。但是,如果在文化的意义上来研究江南儒学,那么现有的江南文化研究就已经可以了,实在没有必要另外标举江南儒学。因此,当我们型塑江南儒学这个研究领域时,儒学的内涵指向不是广义的文化,而是狭义的“学”。借用李学勤“儒学的核心就是经学”[5]的话,江南儒学的研究对象将主要是以经学为核心而展开的儒家学术思想;而置换成现代学术的分类,则是以哲学为视角的儒学研究。不过,在明确了这个基本界定后,必须马上跟进的说明是,由于江南儒学的研究是一项与地方区域具有高度相关性的研究,而无论是作为传统知识意义上的经学,还是作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江南儒学不仅在知识上与其它门类具有非常粘连的关系,比如传统意义上的经史并重几乎是江南儒学中无法分割的研究对象,而且在实践上延伸到必须其它知识门类加以分析的领域,比如陈子龙所讲的“风教”就很大程度上溢出了哲学的分析范围。
由此出发,江南儒学的研究将聚焦于呈现思想的儒家思想者的文本分析,以期发现与阐明那些型塑江南性质与特征的内容,但同时又会兼顾这些思想文本与它的现实境遇之间的互动。在处理后者的问题时,也许我们的研究将溢出思想文本的哲学分析,延伸到其它文献的处理,以谋取思想史研究的效果;甚至不排除田野调查,尤其在进入明清以后,前文所注即是一个例子。毫无疑问,具体的过程将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而决定,不宜也难以作清晰的规定。此外,当我们对江南儒学研究中的儒学概念作这样的自我限定,除了儒学本身具有这样的依据外,一个最根本的考量是源自专业的操作。术业专攻也许是一个逃避研究复杂问题的遁词,但的确是一个方便操作的理由,况且专业精神终究也是现代学术分工的基础。当然,对江南儒学作这样的自我限定,决不意谓着其它视角的观察就不属于儒学研究。前文对“风教”的着意强调,实际上就包含着对儒学作广义文化意义上的理解。换言之,多视角的观察不仅是不排除,而且正是发现与呈现多样性的根本路径,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的研究也将努力尝试。
[1]关于南北经济中心的转移及其完成的起点与终点,历史学界的看法不完全一致,社会与文化的中心也是如此,这里的讨论且取安史之乱为起点,明代为终点,但具体到江南儒学的孕生与演化,后文将结合江南的形成具体而论。
[2]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共用三章,即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章来梳理论证南移的问题,其中梳理南移现象与过程集中在第三十八章“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上)自唐至明之社会”。
[3]森正夫《陈子龙的江南论》,收入氏著《“地域社会”视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为中心》。
[4]晚清江南因太平天国战乱人口大减,有大批河南移民落户至浙江长兴与安徽广德之间,笔者的父母都属于这些移民的后裔。据移民至长兴的笔者父系族谱,至笔者已是第八代。在改革开放以前,河南移民基本以村为单位聚居,语言与文化殊于当地。虽然这些移民村落基本分布在县域中相对偏僻落后之处,经济水准明显低于当地社群,但在文化上却有着某种属于集体无意识的优越感,一个最显明的证据就是他们都把当地人称为“蛮子”。这也许不一定构成非常强有力的证据,但至少可以提供一个田野性质的佐证。
[5]见《光明网》2012年6月23日载:《李学勤: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
end
资料:上海书店出版社
编辑:段鹏程
上观号作者:书香上海